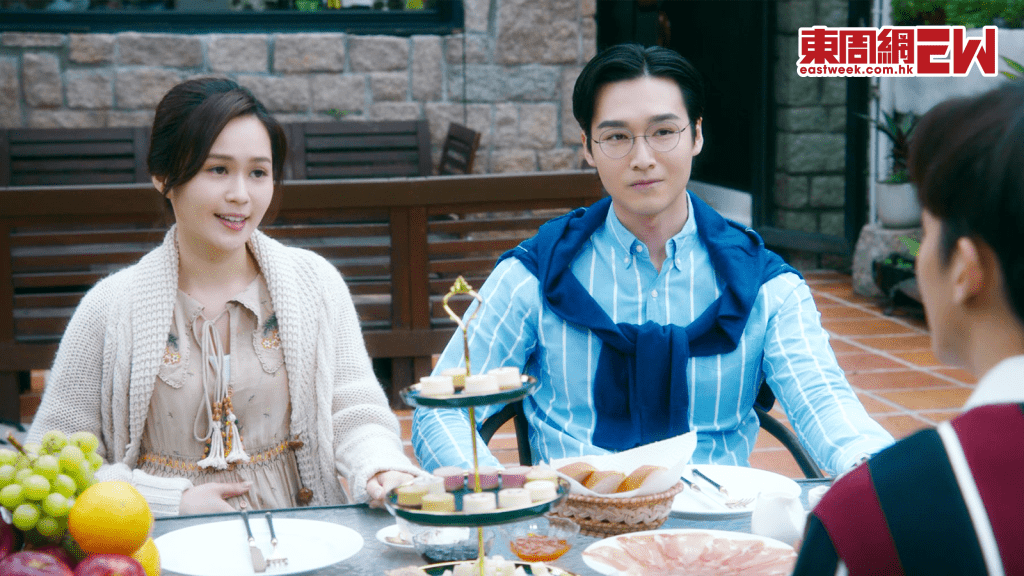相信疫情人人要戴口罩出街的日子,大家都不陌生。即使口罩令已經相隔兩、三年,生活看似回到正軌,但有些感覺,其實一直殘留着。
例如,你有沒有試過在疫情期間認識一個人,長時間只看過他戴口罩的樣子,直到某一天,彼此終於在沒有遮擋的情況下見面,卻發現—完全認不出來?而且不是「差一點點」,而是跟你腦海裏反覆想像過的那張臉,判若兩人。這裏沒有漂亮與否的問題,而是那張臉,和你曾經為它編織過的想像,根本對不上。
這件事,其實在我身上發生過不只一次。
我居住的大廈有一位管理員。疫情期間,我每天進出都會見到她。她戴着口罩,聲音溫和,說話方式很有親和力,不知為何,我總覺得她很像當時常常出現在新聞裏的張竹君醫生。久而久之,我腦裏已經默默「確認」了:她就是長那個樣子。
直到兩年後的一天,我如常落街放狗,經過管理處,聽到熟悉的聲音叫我:「黃小姐。」我轉過頭—吓?她是誰?那一刻,我的腦袋完全對不上。明明聲音、語氣、稱呼方式都對,但臉不對。我記憶中,那把聲音,是屬於那位「張竹君樣」的管理員。那也是我第一次清楚意會到,原來自己曾經為一張長期被口罩遮住的臉,設計過一個如此具體、卻完全錯誤的版本。
疫情期間,我也第一次參加法會。因為人多,法師和工作人員大多數時間都戴着口罩。即使疫情過後,這個習慣仍然持續。直到今年,我才第一次真正看到一位認識了5年的法師,以及一位師兄的完整樣貌。
老實說,法師的臉,我到現在每次見到,還是會在心裏疑惑:「是同一個人嗎?」而那位師兄帶來的衝擊更大。5年裏,我早已在腦海中為他創作好一張臉,並牢牢記住。當天真正看到他的全臉時,我整個人呆住了。我很認真地看着他,辨認他,提醒自己:要重新記住,眼前這一個,才是正確的版本。
這個過程,是最艱難的。明明大家已認識很久,有共同的回憶與互動,但那些熟悉感,卻一時間無法黏合在這張突然出現的陌生臉上。最後,我花了好幾個月,才真的把自己原本安放在口罩下的那半張臉,慢慢洗掉。
後來我才知道,這其實未必是我特別面盲。心理學研究早就指出,人類在辨識不熟悉的臉孔時,非常依賴整體輪廓與下半臉的比例,而口罩遮住的,正正是建立臉部記憶最關鍵的部分。長時間只看到眼睛、聲音與行為,大腦會自動用想像補完一張臉,並把那張「假想的臉」存進記憶裏。於是,當真正的臉第一次出現時,大腦不是更新,而是衝突。
這大概是後疫情時代一種很獨特的經驗。只看見一部分的時候,我們很容易替別人補完剩下的樣子。只是那些猜測,未必是真的。也許這段經驗提醒我的,不只是怎樣去認人,而是—在還沒看清之前,少一點想像,多一點保留。

長時間只看到眼睛、聲音與行為,大腦會自動用想像補完一張臉,並把那張「假想的臉」存進記憶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