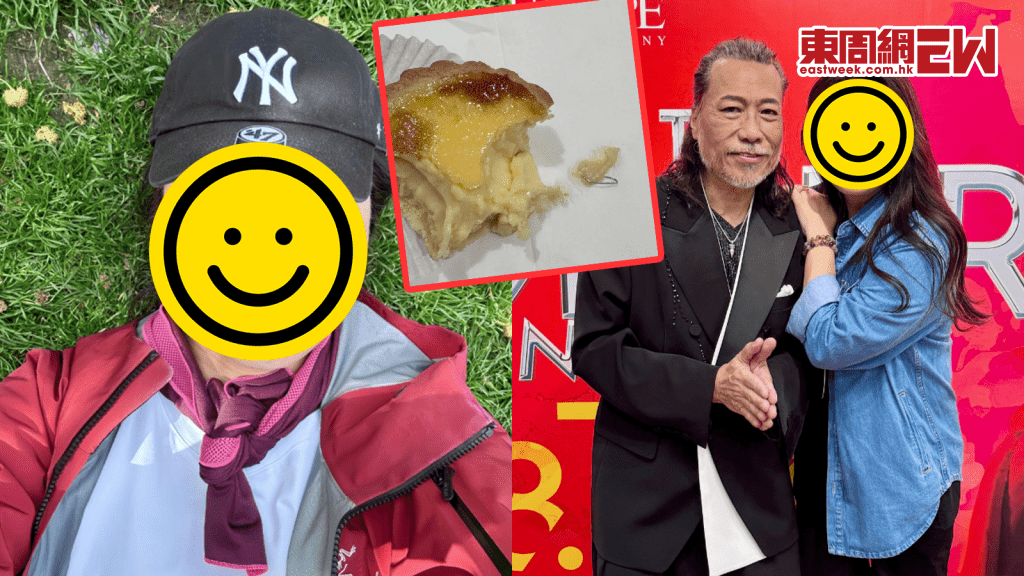兩年前九月,終審法院就社運分子岑子杰的上訴案作出終極判決,雖然大體上並不認同同性婚姻,卻有一項判他勝訴,就是裁定根據《香港人權法案》,政府有「積極義務承認同性伴侶關係,所以要確立一個替代框架去履行與此有關的權利和責任。」這可是個燙手山芋,等如叫政府在承認與不承認之間「中間落墨」。鑑於香港社會普遍反對同性婚姻,這任務極其艱巨,最近政府提出的替代框架被立法會猛烈抨擊,那邊廂同志平權人士又不收貨,可見問題的複雜性。

處理同性伴侶關係,至今仍是個燙手山芋,圖為2024同志遺產平權案裁決。
今天世界各國對這問題的做法大抵分幾類。第一類是已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、地區,現在約有三十多個,大都是思想較開放的歐美地區,亞洲就只有台灣,聽說泰國最近也合法化了。第二類就是接受「民事結合」(civil union)的地區,這種關係不等如婚姻,但也可以享有某些合法婚姻賦予的權利。而第三類就是本地不承認,但接受當事人在外地的同性婚姻證明,而據此給予他們某些權利。終審庭並沒有就政府應採取哪種做法作出指令。終審庭所援引的人權法第十四條,內容十分簡短概括,條文大意是任何人之私生活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,而對於此等侵擾「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」。以此作為裁判的依據其實有點牽強,但好在法庭給予政府酌情權去界定這等權利的範圍。看來憲制及內地事務局是採取了上述第三種做法(登記外地的同性婚姻證明),並把同性伴侶「私生活」所享有的權利局限於醫療和後事、殯葬有關的範圍,例如往醫院探視伴侶、獲取伴侶的醫療資訊及參與醫療決定、認領伴侶遺體、申請死亡證和火葬許可證等。
富爭議性和與實質利益相關的課題,如配偶福利、遺產和公共房屋承繼權等未有涉及。讓同性伴侶名正言順地登記外地結婚證明,從而享受某些法定權利的做法,無論政府怎辯解也是對同性婚姻間接承認。這便冒了今天香港社會的大不韙,而且政府事前沒半點公眾諮詢摸底,法庭定下的限期臨近才匆匆提出,立法會諸公對此大動肝火,也是必然和可以理解的。
我自己啄磨,範圍既然已收窄至醫療和身後事兩個範疇,便根本沒有必要把甚麼外地同性婚姻證明牽扯進來。最簡單的做法是容許任何人申請指明一名並非其配偶或親屬的人士,性別不論,可以合法地處理申請人以上各種醫療和身後事宜(雖然這類人士大都沒有異性配偶,但為了避免爭拗,可以不容許有合法在生配偶的人作出此項申請)。這個方案當然不會獲岑子杰那邊的人支持,但若過得了法庭、立法會和公眾那幾關,便值得一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