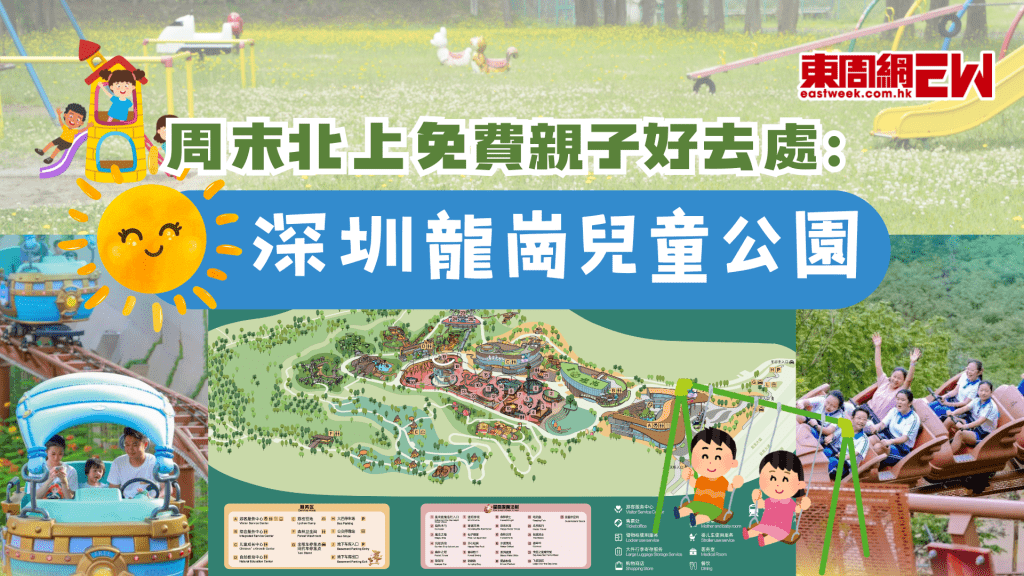上個月我看了三場帶有口述影像的電影,沒想到是很特殊的經驗,甚至讓我這個電影系畢業生對敘事手法有新的認知。
口述影像主要服務對象是視障人士,宣傳上當然也針對他們,除了看電影時會注意到某些場次提供口述影像選擇,多數人並不知道這項服務在本地發展已有十年。
香港以外,audio description(簡稱AD)在美國發展得比較早,90年代已有口述影像電影,另外還有一些電視節目、劇場和博物館都有這項服務。如果你是Netflix用戶,可能發現部分節目帶有AD功能;據說連加拿大成人片網站Pornhub也提供AD選項。
香港起步遲,卻追得快,口述影像近年備受關注,院線支持下電影場次越來越多。我上月看的三部是電影文化中心搞的專場,全部都設映後談東。看完《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》,我問黃浩然導演怎麼看待口述影像員的語氣,他和AD團隊都認為配音員應盡量保持中立語調;這其實也是口述影像一貫做法,好處是讓聽者有更大想像空間,壞處是冷靜的語氣可能打斷情緒飽滿的場景。
我之前一直糾結配音員的語調該如何落墨,看完三部口述電影,我發現語氣只是整個「表演」的一部分,口述影像員說話的節奏,甚至音量都有學問。在一個電影場景裏,如果燈光是語氣,那剪接就是節奏,而運鏡便是音量。當然這只是籠統的歸納,如何把影像翻譯成聲音,是個大課題。
不過,對視障人士更重要的還是描述具體內容。我看了許鞍華《詩》,紀錄片拍攝現場沒有太多設計,有時更有些雜亂,甚麼該描述甚麼不用講,那是撰稿員的功夫。譬如說,受訪者的家居環境能反映他的生活水平和個性,觀眾看一眼便對人物心中有數,但用語言描述就累贅了。有視障人士映後分享,一部電影就算有口述影像,有時也要入場聽幾次,因為訊息太多,一次未必能全部消化掉。
令我感受最深的是《燈火闌珊》,開眼的年輕人都未見過滿街霓虹燈的香港,部分視障人士更是連霓虹光管是甚麼樣子都沒概念。片末霓虹燈牌亮起的一瞬間,他們真的能通過語音「看見」嗎?燈光熄滅一刻的落寞,他們又能感受到嗎?但願他們能看見。

口述影像主要服務對象是視障人士,在本地發展已有十年。

許鞍華的《詩》拍攝現場沒有太多設計,有時更有些雜亂。

《燈火闌珊》中滿街霓虹燈的香港。

視障人士真的能通過語音「看見」霓虹燈嗎?

電影《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》有提供口述影像選擇場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