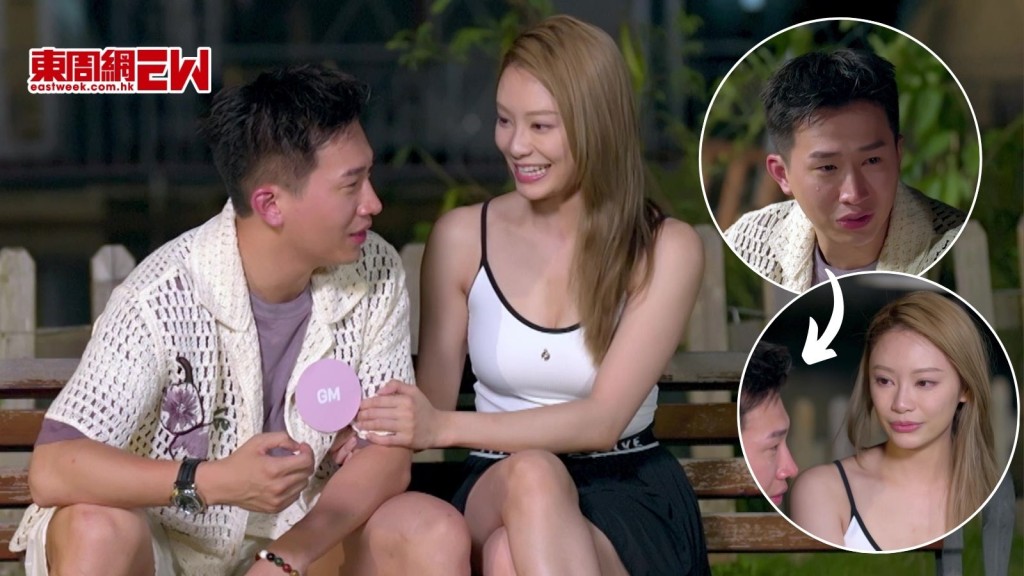發佈時間:12:30 2025-08-17

國際刑警上月撤銷一道全球有效的「紅色通緝令」,終結對保羅華生(Paul Watson)橫跨十三年的全球追捕。
保羅華生並非十惡不赦的罪犯,而是一名激進「海洋守護者」,環保界視這次解除通緝令是遲來的正義,他自己則認為是「結束政治逼害的勝利」。保羅華生四十年來橫跨南極、太平洋等非法捕撈熱點,衝撞捕鯨船、擲出惡臭彈,對抗破壞海洋生態的國家,以激進手段獲得國際媒體關注,也引來各國政府「追殺」。
雖然紅色通緝令已撤,但包括日本、哥斯達黎加等國家仍保留對保羅華生的緝捕令。相反,保羅華生已揚言,計劃重出江湖,繼續這場「海上正義戰爭」。

「對我來說,這是一次小小的正義勝利;對鯨魚來說,卻是一次重大的正義勝利。」保羅華生在國際刑警撤消其紅色通緝令後,透過其創立的基金會發表「勝利宣言」,又形容這是結束十四年來出於政治動機的逼害。
在歷經多年訴訟與國際之間的角力後,國際刑警檔案監控委員會(CCF)於七月下旬,以通緝具政治性、指控不成比例等因素,認定通緝不符制度要求,決定正式撤銷對保羅華生的紅色通緝令。然而,有評論提醒,即使紅色通緝令已被撤消,但部分國家的緝捕令尚未解除,保羅華生踏足相關國家仍可能被拘捕。
現年七十四歲的保羅華生,擁有加拿大與美國雙重國籍,是海洋保育與動物權益運動中最具爭議且引人注目的代表之一。他自一九七一年參與反對美國在阿拉斯加阿姆契特卡島(Amchitka)核試驗的抗議行動,便開始涉足環保行列。當時年僅二十一歲的他,參與了一個名為「Don't Make a Wave Committee」的反核行動小組。
他與其他成員一同駕船前往核試驗區抗議,雖然該次行動未能阻止核試,但卻為全球環保運動樹立了典範,這個反核小組其後正式改名為綠色和平(Greenpeace),並成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環保組織之一,亦開啟保羅華生的環保路。
主張直接衝撞捕鯨船
可是,在多年後,他因不滿綠色和平的「和平抗議」路線過於溫和,隨後創立更加激進的「海洋守護者協會」(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),主張直接行動衝撞非法捕鯨船,以激進但不致人受傷的方式,阻止海上非法獵殺,開始其「保育戰神」的戰鬥路。
保羅華生採用的「積極非暴力介入」策略,包括駛向捕鯨船撞擊船舷、投擲煙霧彈與惡臭彈、阻斷非法漁船航道等,旨在強制執行國際條約與保育法例。雖然他聲稱不會傷人,但其衝撞與擾亂行動,多次引發國家訴訟與外交抗議。
一九八六年,他策劃船隊成功使冰島兩艘捕鯨船於雷克雅維克港沉沒,引起冰島政府強烈譴責,指這是「恐怖主義行為」。這除了是他首度引發國家級譴責之外,亦令他從「激進環保分子」躍升為國際爭議人物。

他的團隊其後在二○一○年在南極與日本捕鯨船「Shonan Maru 2」對峙,日本因他在次行動中下令投擲「臭彈」,於一二年向國際刑警申請對他發出紅色通緝令;同年哥斯達黎加亦提出類似引渡請求,導致保羅華生於同年五月在德國法蘭克福被捕,及後在保釋期間潛逃,正式成為通緝犯。
紅色通緝令雖非正式拘捕令,但足以讓世界各地的執法部門對他保持高度警覺。他多年來都不敢踏足多國領土,包括自己長期活動的歐洲與拉丁美洲,行程處處受限,即使要參與國際保育會議、記者會,都只能透過錄影或網上方式「遙距現身」,他形容這段歲月是「無疆界的政治逼害」。

日本丹麥多國的眼中釘
保羅華生深知自己的行動觸犯多國利益,長期成為日本、哥斯達黎加、德國、丹麥等政府的「眼中釘」,雖然在潛逃期間繼續在全球航行,但直至去年七月,他在格陵蘭努克(Nuuk)被丹麥警方拘留,日本政府提出引渡,經過五個月羈押,丹麥最終拒絕引渡,理由包括日本的起訴帶有政治動機、缺乏引渡協議等因素,隨後將他釋放,保羅華生遂返回巴黎居住。
保羅華生雖然是著名保育團體「海洋守護者協會」創辦人之一,可是他自三年前與協會出現重大理念與方向分歧,最終被董事會排除於組織決策之外。為延續自己倡議的「直接行動」保育哲學,華生隨即創立「保羅華生船長基金會」,繼續針對非法捕鯨進行打擊。

根據「保羅華生船長基金會」二三年的報告顯示,其收入折合一千二百萬元(港元,下同),全數來自個人與私人企業捐款,但未有詳細交代名單,只有導演占士金馬倫、維珍集團創辦人李察布蘭遜曾公開聲援他的行動。
保羅華生揚言,這場「海上正義戰爭」尚未結束,正計劃重出江湖。支持者稱他為「海洋守護神」,視之為無畏的英雄;反對者卻斥他是「環保海盜」;他本人則堅持做自己「我不是來讓大家喜歡我,而是要讓地球活下去。」
《國際捕鯨公約》形同廢紙
儘管全球早於八十年前已簽訂《國際捕鯨公約》( ICRW),並實施「商業捕鯨暫停令」,但時至今日,捕鯨活動依然在部分國家如挪威、日本、冰島持續進行。
事關公約不是永久禁令,容許會員國對特定條款提出「保留」,拒絕受其約束。例如挪威在當年曾保留對暫停令的執行,得以持續商業捕鯨;冰島則在九二年一度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( IWC),十年後即使重新加入,亦不接受暫停令約束。
除此之外,科研捕鯨亦是制度最具爭議的漏洞之一,日本就長年利用該規例,每年在南極及西北太平洋水域捕殺上百條鯨魚,其鯨肉亦隨後流入市場,最終遭裁定違反國際法,其後更索性退出IWC,公開恢復商業捕鯨,轉戰自家近海水域,聲言「不再受無效制度束縛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