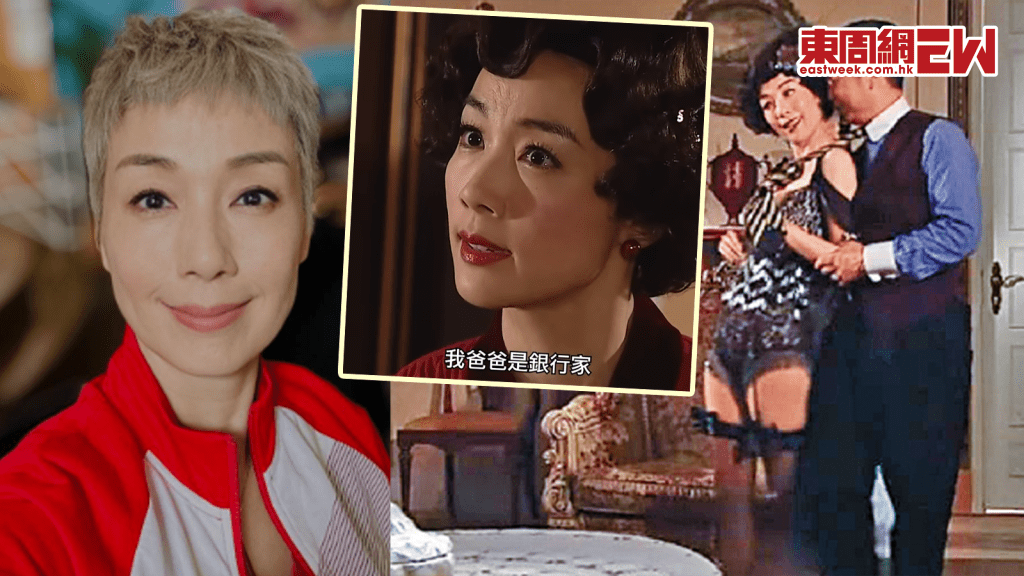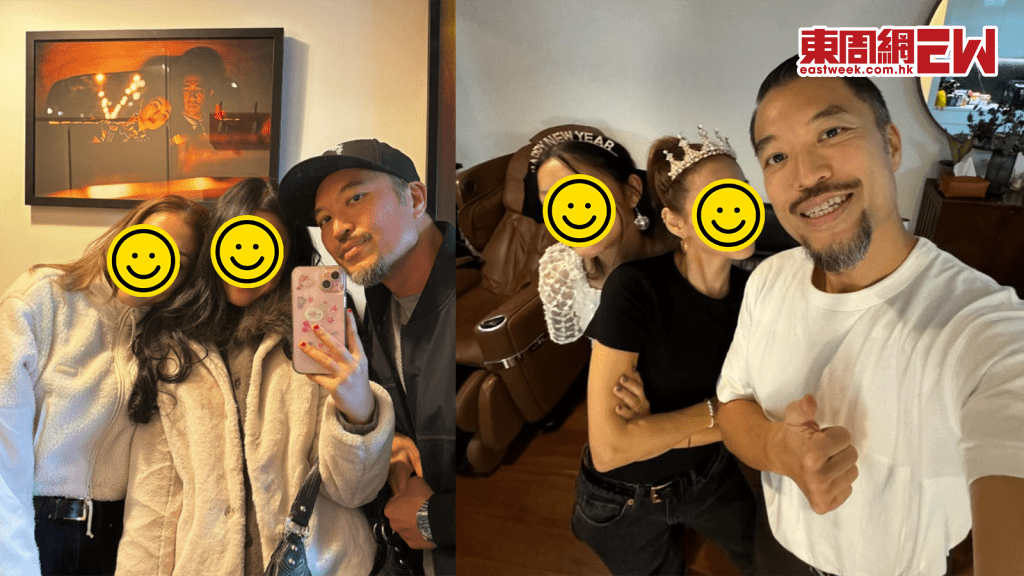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看「流動的盛宴──中國飲食文化」展覽,導賞老師說到「禮食同源」,我反射性想起《禮記》的「飲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」食色性也,是生存和繁衍的本能,但當飲食不只是為了活命,便形成了文化。
禮食同源的「禮」指祭祀,最近讀張競《中華料理の文化史》中文版,提到祭祀時要為神明奉上全隻牲畜,祭後分食,才知道中國人食內臟的習慣可能源於祭神。
祭祀影響飲食習慣,也影響文字。香港故宮展出文物以食器為主,先秦時期食器很多也是禮器,用法講究。其中一種禮器叫「豆」,主要盛放醃菜和醬汁,展覽說明牌上引用《說文解字》:「豐,豆之豐滿者也。」說有學者認為「豐」就是豆上放滿食物的樣子。這個說法其實也有爭議,因為金文中「豐」字從「壴」不從「豆」,儘管也與祭祀相關,卻是樂器而非食器。
導賞老師接着講到倒酒器物中,曲柄的斗和直柄的勺,關係到「斟酌」二字。這兩個字很有意思,先看《說文》,前者「從斗,甚聲。」後者「從酉,勺聲。」斗和酉都與飲酒有關。「斟」有傾注之意,粵語就保留了「斟酒」這個說法;「酌」是「盛酒行殤」,即斟酒勸飲,亦可簡化為飲酒之意,如李白的《月下獨酌》。
諸葛亮《出師表》裏寫「斟酌損益」,「斟酌」二字放在一起如何演變成考慮之意呢?較多人支持的說法是,斟是倒酒,酌是飲酒,即前者增多後者減少,按自己酒量掌握好飲酒的分寸,就是「斟酌」,可見古人對飲酒還是有所節制,並非像電視劇中一味豪飲。
展覽第二部分叫「胡食風尚」,介紹與中亞和西亞飲食文化的交流,除了食器也有食材,所有帶「胡」、「番」、「洋」字的食品,如胡蘿蔔、番茄、洋蔥,都是不同時期輸入的外來農產品。然而,影響中國近代飲食文化最大的進口食材,卻偏偏沒有以上的三個字。辣椒於明末清初才傳入,顛覆了川菜和湘菜等菜系,至今中國亦成為了全球最嗜辣的國家之一。
後面的「遊宴之樂」,用大白話說就是「野餐」。文人雅士多愛山水之間聚會,唐代李白與堂弟桃花樹下宴飲,寫下《春夜宴桃李園序》;北宋蘇軾被貶黃州,與友人二遊赤壁,作前後《赤壁賦》,都是千古名篇。是次展覽展出的《夜宴桃李園圖》和《赤壁夜遊圖》均繪於清朝,可惜未有任何東晋「蘭亭雅集」相關展品,稍嫌美中不足。不過看到後面展出的食物提盒和多寶匣,個個獨具匠心,也算彌補了遺憾。

戰國時期的豆

商朝青銅斗

清朝剔紅提匣

夜宴桃李園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