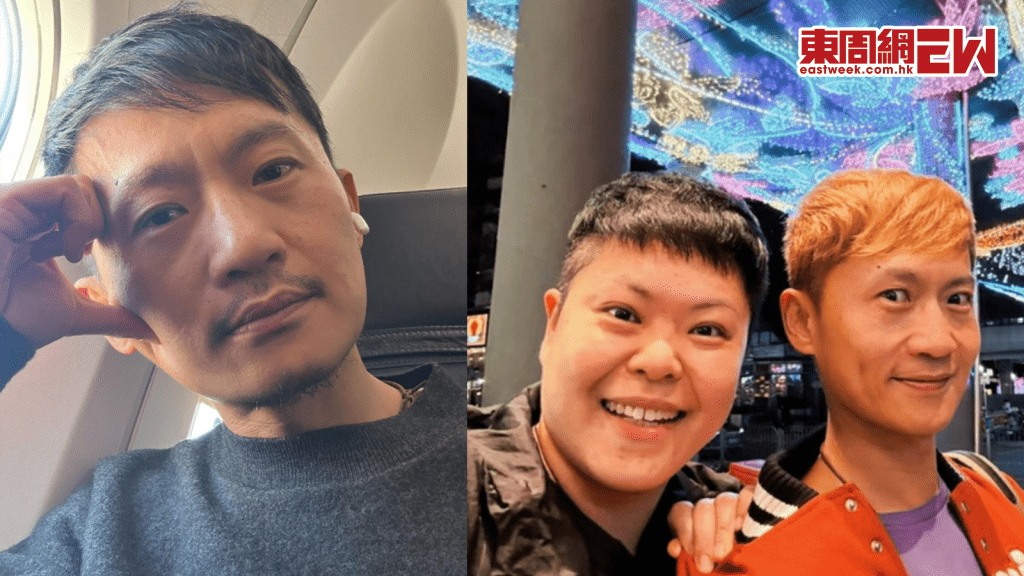發佈時間:08:55 2024-05-26

香港的影視作品不但為公眾提供了資訊和娛樂,同時亦具有很大的影響力,當中創造出來的文化藝術更是一種「軟實力」。
由形象指導、寫作人,以至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副會長等,劉天蘭有說不盡的身份,但都與創作和藝術有密切關連。
她自去年與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展覽,回顧電影服裝的黃金歲月後,引發一個諗頭,希望把香港累積得來的文化瑰寶好好典藏及整理,讓本地表演藝術的歷史得以傳承。
劉天蘭多年來在社會上不同界別都留下腳印,「百足咁多爪」的她興趣多多,「我如BB一樣,是一步步走。」她形容自己是憑努力,逐步建立現有的一切,「我在很正常的家庭長大,不是特別有錢。爸爸很早因為飛機失事離世,當時的我只有四歲,媽媽養大我們三兄妹。」劉天蘭雖然是孻女,卻是最會照顧別人的一個。

元祖級斜槓族
劉天蘭憶述:「媽媽是一個既傳統且很獨立的事業女性,她以前在《新晚報》任報紙編輯。」自言在「好學校」長大的她,中小學就讀聖保羅男女,「我在香港長大,十零廿歲時就跟媽咪移民加拿大,在西門菲沙大學讀書。」大學修讀大眾傳播及電影課程,「後來選擇回流,一回來就數十年了。因為這是我的家、我的根。」七十年代末期, 她回港發展,展開其豐盛的演藝及形象事業。
她從小到大都是循規道矩,「媽媽給我很多自由,讓我尋找興趣,曾建議我和姐姐學鋼琴,姐姐是五級,我則在中一時轉了學結他,之後再轉學Folk Music,開始學唱歌。為人父母應該看孩子的興趣和天分,他喜歡甚麼就讓他去試,試過後,不喜歡就不要逼他。」劉媽媽就是這樣放手讓子女自由選擇發展路向,這亦成為了劉天蘭日後當媽媽的教材。
她直言:「那些虎爸、虎媽是傻的。我女兒Yoyo(岑寧兒),結果也是做音樂。她小時候很喜歡唱歌,音又準,我從來沒有逼過她。」她於二○一三年推出自傳《原來天蘭》,「書內有篇文章是Yoyo寫的,她說『媽媽只是叫我跟自己比較,今天要比昨天好便可以』。」

形象指導、服裝造型總監、演員、歌手、寫作人、跨媒體創作人、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副會長都是劉天蘭的身份,作為元祖級斜槓族的代表,她說:「因為我的性格和興趣很多,機緣巧合下,我的確做了很多不同的行業。如果我蓋棺那天下定論『劉天蘭做過多少事?』真的是十隻手指數不完,但我做得很開心。」她從加拿大回港,先做幕前,同時也做幕後,且更喜歡做幕後。她每樣都有興趣,嘗試不同崗位,得到很多豐富體驗。
性格積極的劉天蘭甚少會感到後悔,「我很正面的, 不喜歡留在負面裏。人越大會越多壓力,因為要照顧的事比較多。要提醒自己能放低的便放低,不是自己沒有能力,但既然請了別人就信任別人,用人莫疑,大家分工。後悔冇問題,但不值得。所以我媽離世前我跟她說『我愛你』,還捉緊了最後數年的相處時光,好好讓她知道女兒的心意。」
劉天蘭自爆曾有廿年吸煙習慣,二○○六年決定戒煙,「一聲話戒就戒了廿多年。中間那段日子個人很繃緊,試過腰痛亦試過生病,因為不懂放鬆,工作總是做到很累,後來學懂停下來再作調整,便是一個進步。我生活的質素不應該被工作或所謂的責任感打倒,失衡是沒有意思。」

只跟自己競賽
「人生最大困難是不夠時間,怎樣面對呢?」劉天蘭感慨道:「只得數十年,那便盡量去面對,這是個哲學問題。最大的問題是世界太大, 只可以在有生之年去盡力做。」她分享其座右銘,「Think Ahead,Plan Ahead,Do Ahead,即是凡事準備多啲,諗多啲,計劃多啲,拍戲太多突發事故,需要更多預備,只要想到最壞的情況,那便天崩地裂都不用怕,盡了力仍失敗亦無話可說,最重要是問心無愧。」
在電影圈打滾多年的劉天蘭,分享對行業近年發展的看法,「大片當然是好,有資源、有合適的條件去拍攝靚的戲是一件事,但電影是中立的,是一個可大可小的媒體,無人說一定要大片才叫電影。從《正義迴廊》開始,近年有十部八部電影都『好見得人』,令人很開心。數量少了便由它少了,這是一個進化過程, 也是社會變遷的過程。」

曾經有很多人認為「香港電影已死」,沒法回復以前的黃金時代,劉天蘭另有看法,「新導演、新演員,已經是新的一代。電影是反映社會、民生,人人(新一代)都很努力,好不容易才開到一齣戲。」
熱愛電影的她將看戲視為娛樂和休息,「我一天可以看兩齣戲。」今年六十六歲的她,還會在工作與工作之間自行歐遊半個月,就是想給自己一些養分。她坦言,直到花甲之年,才開始做運動,「六十歲開始,每星期健身兩次,很勤力。很感恩自己會這樣做。這副機器若然不為它抹油,只可以向下,要抹油才保持長久。自己照顧自己是一種投資,需要時間、金錢。」

不與別人比較
去年為了「無中生有——香港電影美術及服裝造型展」而頻撲,她暫停運動半年,「完了展覽後,體能又要從頭再來,所以我更明白運動有多重要。不過運動也不要跟別人比較,自己跟自己比,身體好了也會開心更多。」
對於未來,劉天蘭在今年書展前將推出一本關於《無中生有》展覽的一個全紀錄,「是為了記錄整個展覽,會有一些幕後花絮,已拍了很多照片,是有備而戰。展覽過程中獲得很多回應和觀眾留下的意見,那些我通通都儲起了。」
她將於六月參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(香港分會)主辦、首次在亞洲舉行的「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、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」國際研討會前的講座「整存 ,再現與詮釋:保育演藝與電影文化背後的故事」中擔任講者,談論在香港彈丸之地,如何有限地保存及典藏演藝的瑰寶,又讓本地的表演藝術文化及紀錄得以傳承下去,這是一門高深的學問。

拍戲就是無中生有
去年香港電影美術學會舉行了「無中生有—香港電影美術及服裝造型展」,劉天蘭指這是協會有史以來最大的項目,「協會於九六年成立,過往曾有開班、講座、聯誼等,這麼大型的展覽已是四、五年前的事。這四個月做了很多場導賞,其中我做了四十場。」
她說:「拍戲已經是無中生有,這是拍戲中再一層的無中生有。我們把它『生出來』才能拍戲。我為我的同僚感到驕傲,拍畢一套辛苦到想死,捱夜、生暗瘡、胃痛、失眠、很大壓力。」她直言:「很老土地說一句,今天是我們以往累積下來的結果,即值得保留的文化,要珍惜它。能留低的都是好的,差的早已被淘汰。典藏是有教育意義,以戲服來說,旗袍、迷你裙、古裝等,那種質量是現在買不到的。它是根據電影故事或劇本而創造,天馬行空甚麼時代也可以。」
「香港不夠地方擺放,不論是捐出去或送出去又好,相關物品有時會四散。片廠未必有空間擺放,所以不是所有都能保存,已丟掉了很多,我們聽見都傷心。」戲服有助說故事,她認為是很Magical,「可展示出人物性格、社會地位、經濟條件、品味、職業、年紀、身份等,不用開口已有感覺,亦能幫助演員入戲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