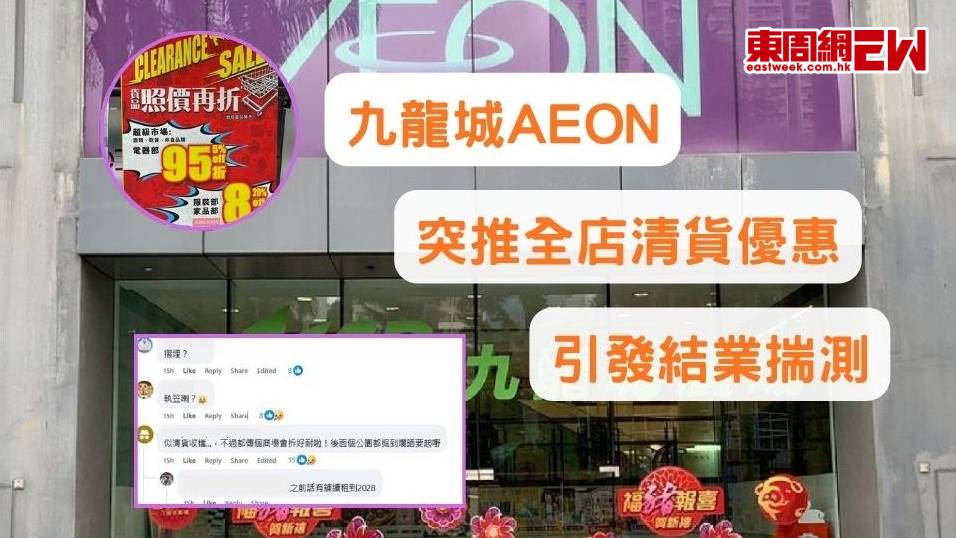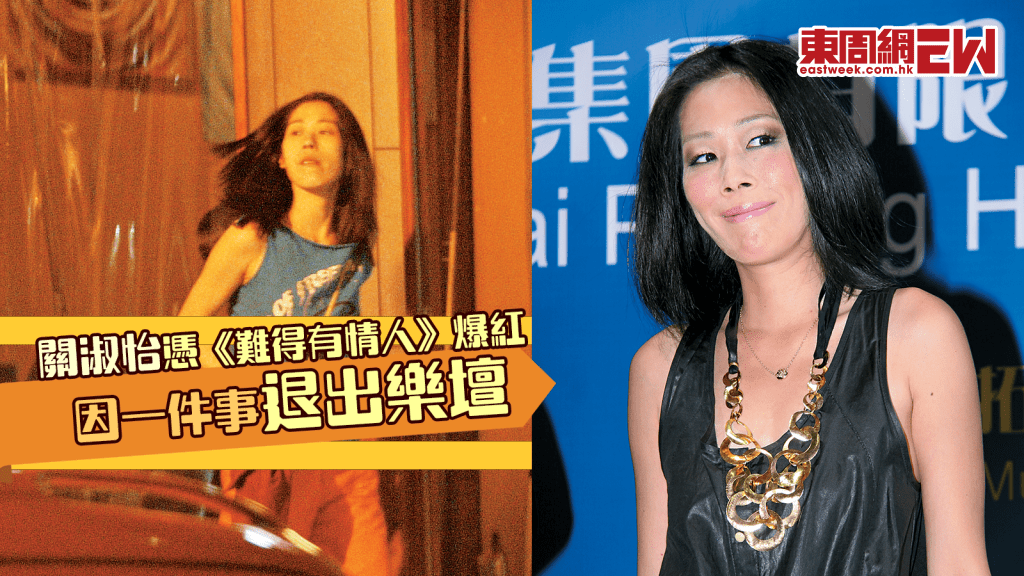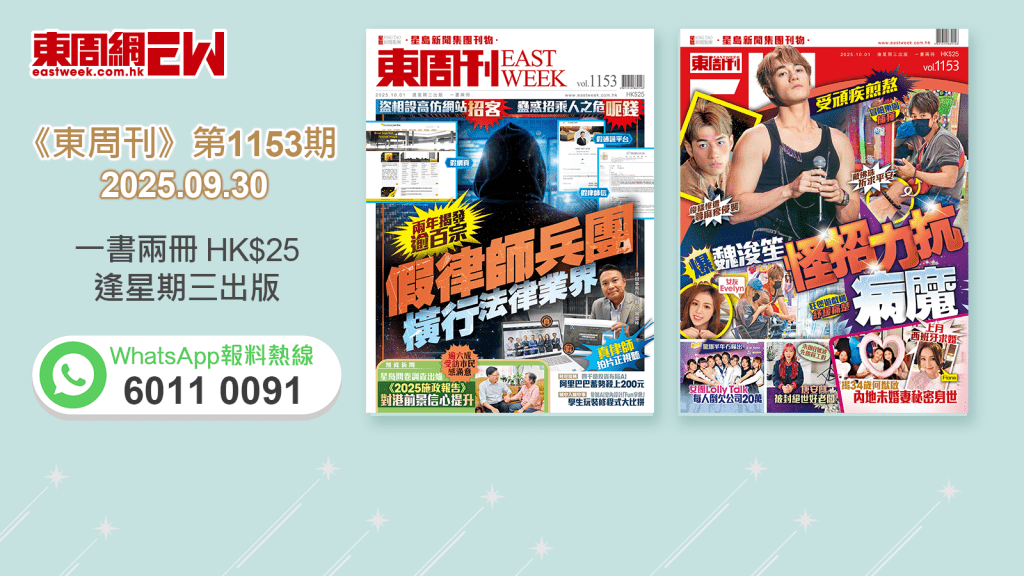看過九月初紀念抗日勝利大閱兵,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復,馬上又恭逢國慶,不禁要奮筆疾書此刻的心情。

每年10月1日,在金紫荊廣場都會舉行國慶升旗儀式。
我輩生於上世紀中葉、英國治下的香港人,在成長期絕大部分很難有甚麼家國之情,理由很簡單—當時的「家國」並不令人嚮往。新中國一窮二白,加上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如反右、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,百姓的生活十分艱苦。當時的情況我是親身經歷過的,文革那些年,還在唸小學的我經常要伴着母親運送生活物資和藥物到廣州,分派給親戚。他們個個衣衫襤褸,面有菜色,大街上只有公交和單車;商店淨賣些像垃圾一樣的貨物。廣州已算是經濟較好的城市了,其他地方的情況可想而知。
反觀香港,一般人雖沒覺得生活很優裕,但與內地相比已有雲泥之別。當時的「宗主」仍是個「日不落」的大帝國,而且英國殖民政府較其他殖民國家聰明,董得善待原居民,表面化的歧視和欺壓並不多見,所以那時代的香港人是十分擁護和嚮往大英帝國的,不會被指為不愛國。我自小愛讀中國文學,但那是對一種古老文明的珍視,一邊欣賞它,一邊哀悼着它的逐漸消亡。
以我而言,對國家漸有認同感,始於八十年代初。那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大業起步才幾年,全國上下已彷彿在呼吸不一樣的空氣了。香港人也開始感覺到,這個號稱是「共產」的政府,為了改善人民生活,竟可以拋棄僵化的意識形態,改轅易轍。我們開始想,這個國家有望了!而之後的日子裏,香港也大大地得益於國家的開放,成就了自己的經濟騰飛。香港主權在一九八四年拍板回歸,再加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,雖然曾引起信心危機和很大一波移民潮,但中國的持續開放和急速發展,畢竟挽回了香港人的信心,主權在九七年順利過渡,當時社會一片昇平。
就算在那個火紅年代,也沒有人料到國家竟能在三四十年間發展到今天這個架勢。我自己及所有久經蒼桑的上一輩中國人,在有生之年可以看見自己的國家終於強大起來,是何等幸福的事。而且「國力」這東西是有真實質感的:去年第一次開着我的比亞迪電能車在路上飛馳,親身體會國產汽車的先進及性價比,「獲得感」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其實除了國家在經濟、軍事及科技上的成就,更值得我們驕傲的,是在今天這個戡亂無常,是非顛倒的世界,中國正演變成一股錨定世界、真正珍視和平的強大力量,世界亦開始對我們改觀,開始「發現」中國。當別人都故步自封而成為弧島,我們敞開胸襟,與全世界人為善。而中國的偉大,才剛剛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