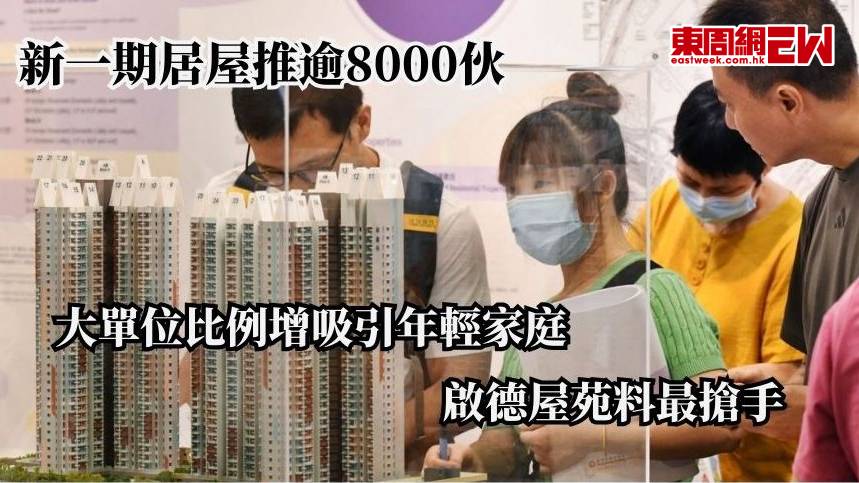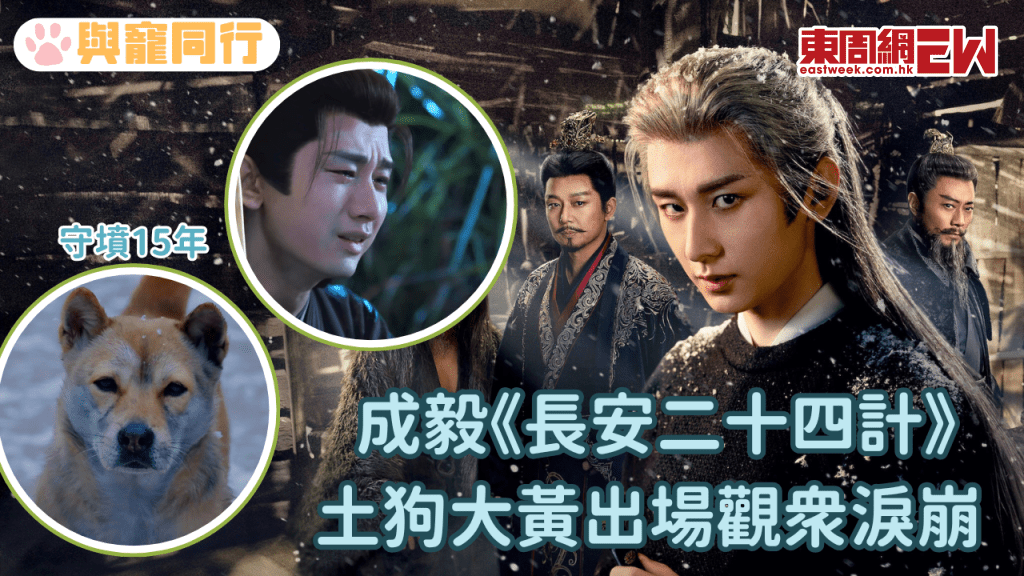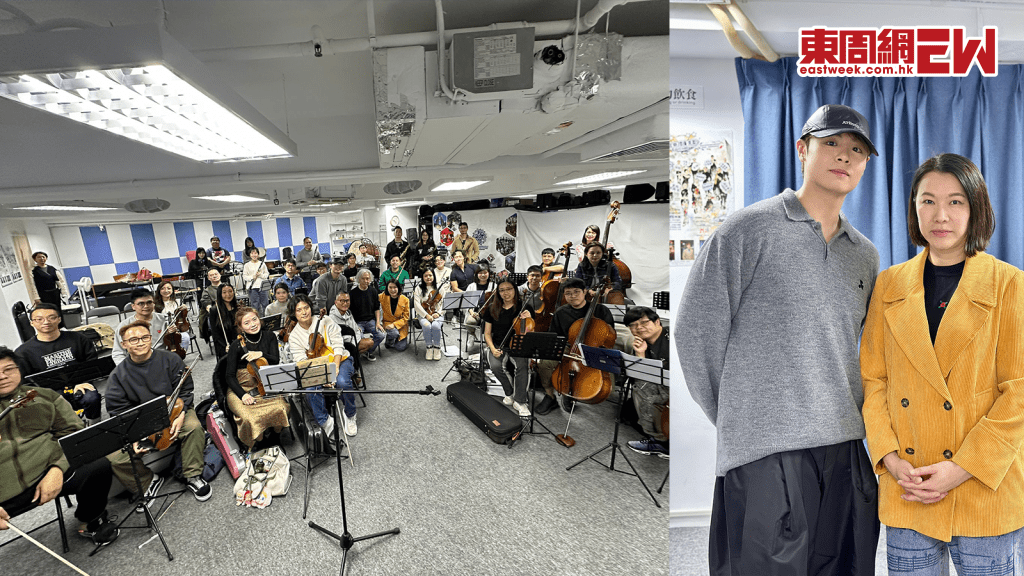在今屆奧斯卡奪得最佳電影、導演、編劇等幾個大獎的Sean Baker在領獎台上向全球觀眾,為瀕臨滅亡的電影院行業發出靈魂的呼喚,節錄如下:「我們都是在哪裏愛上電影的?在電影院。在那裏,我們一起哭,一起笑,一起噪動,一起沉默。尤其在今天這個紛亂和分化的世界,那是一種不能在家裏得到的體驗。今天電影院行業正面臨前所未見的危機,特別是一些獨立經營的電影院。在疫情中美國失去了千多家電影院,看來倒閉潮還會繼續壞下去,我們快將失去我們集體文化裏一個重要部分。」

嘉禾海運戲院最後一日營業,完場後拆走招牌。
這番話,也正好形容香港今天的景況。去年有六家電影院結業,今年還未過半已再添幾家,情況似乎還未見底。其實串流平台的興起老早已預示電影院的式微,但想不到的是,一場世紀疫情把這個過程催快了幾倍,疫情粗暴地把人們關在家中,變成電視和串流平台的俘虜。
「電影院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」這說法我同意,但它其實也有世代之分。今天Z世代是由社交平台、YouTube和Netflix陪伴成長的一代,宅在家一點也不悶,電視已少看,更何況要花錢去電影院看戲?對他們來說,電影院從來不是他們文化的組成部分。Sean Baker說媽媽在他五歲時帶他進電影院,之後便愛上了,所以他呼籲為人父母的,拜託多點帶子女進戲院,自小養成去戲院看戲的好習慣。我唯有祝他好運。
對我們這代人來說,戲院的觀影體驗,的確是無可替代,也承載了無數集體回憶。最教我懷念的,是那些專為放電影而設計(purpose-built),樓底特高、起碼有數百座位的大戲院,如利舞台、東方、豪華和海運等。利舞台的裝潢是歐洲歌劇院的風格,豪華的程度自不待言;灣仔菲林明道的東方戲院雖然不大,但也是富有歐陸情調的單棟式建築,記憶裏淡綠色的四壁有童話仙子的浮雕。我記得小時候一定要爸爸帶我提早進場,因為特別喜歡看戲院(尤其是最近結業的海運)那幅紅色大絲絨 簾幕。這簾幕(較豪華的還有波紋皺摺)開場時緩緩升起,這時場內燈光漸暗,裏面另一幅較淺色的簾幕在投影機映照下從兩邊打開,露出熒幕。我們這才滿有儀式感地開始看戲。這種體驗,恐怕已在世上絕迹了。
對於美好的事物,我們永遠都是在它們快要消失時才去欣賞,或憑弔。快要關門的戲院,通常會像瀕死的人一樣有一場迴光返照,全院滿座,擠滿了來打卡和看最後一場戲的人。政府一年一度的「全港戲院日」過後,戲院又回復寂靜,因為不少只圖省點錢的觀眾,心裏都在說:明年再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