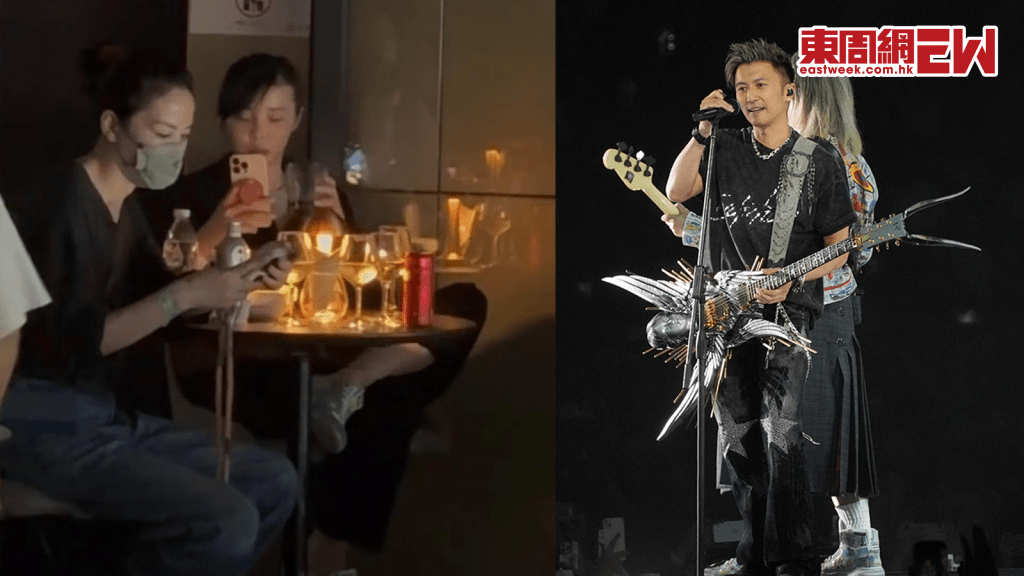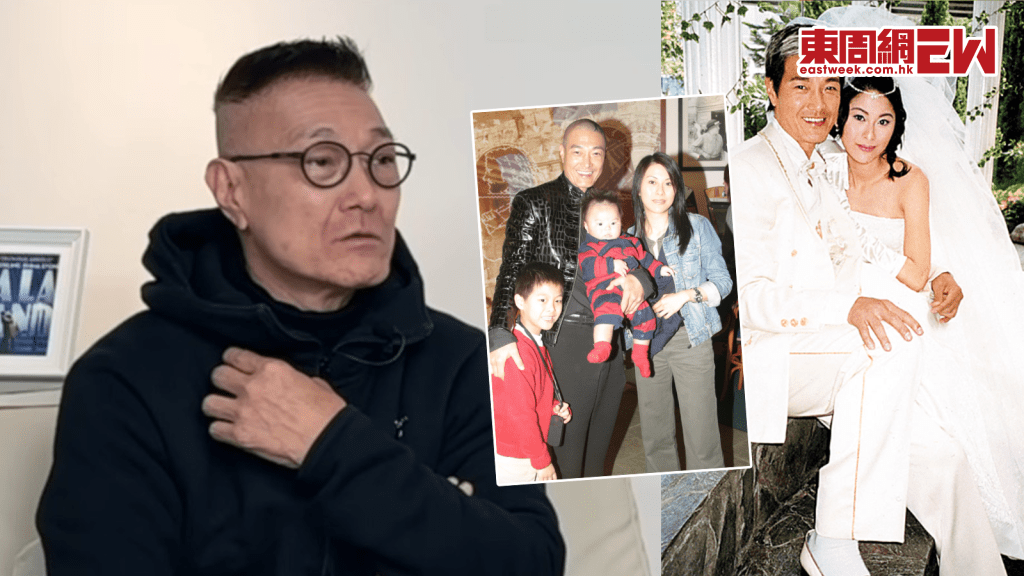猶如中古歐洲所流行的哥特式藝術,兼具神聖性與黑暗性,於創作中雜揉恐怖與超自然的元素,在當代藝術中的黑暗美學,亦常以超越人類視野的「異界」為核心,藉由恐懼、不安、神祕等情感觸發觀者的哲思。
此一創作取向,與藏傳佛教藝術中的「忿怒相」與護法、本尊神祇圖像形成跨時代呼應。兩者皆以非人形象為載體,卻在文化脈絡與精神性上呈現迥異的敘事路徑,形成別具意義的對照和思考。
在密教藝術的世界,常透過諸多神秘的符號與形象,構築儀式性的視覺體驗。尤其是藏傳佛教藝術,在探索人性的議題上,要更加的深入與直白。當中所謂黑暗美學的體現並非純粹的恐怖展示,而是宗教哲學的視覺化實踐。例如諸本尊所示現的忿怒相,多以獠牙、火焰、骷髏飾物等駭人形象示現,實質承載着「降伏煩惱」的隱喻。其猙獰面貌是對世俗執念的震懾,同時象徵破除無明的智慧之力。這種「以惡制惡」的表現手法,將黑暗轉化為通往解脫的媒介,展現神聖性與暴力美學的悖論共存。
而在現代藝術中,黑暗美學常常被用來挑戰觀眾的視覺和心理感受。藝術家通過使用詭異的形象、暗色調性的色彩或扭曲的形式,來引發情感的共鳴。這與藏傳佛教藝術中的表現手法有着相似之處,兩者都試圖引導觀眾進入一個深邃的思考空間,促進對自我和世界的反省。但當代創作不追求宗教救贖,而是直視人性中的陰暗面,將焦慮、孤獨、對未知的恐懼轉譯為視覺語言。
儘管脈絡殊異,兩種藝術形式皆證實「黑暗美學」超越時代的感染力。藏傳佛教以威儀喚醒信徒對神聖的敬畏,當代藝術則以異色喚起對存在本質的反思。兩者的交融不僅豐富了藝術的內涵,也促使我們思考在當前社會中,如何面對內心的黑暗與掙扎。通過深刻的感知探索,藝術不僅是一種表達,更是一種靈魂的救贖與啟發。

《非人異典特展》,2025年,台北d/art畫廊。

《四臂大黑天唐卡》,18世紀,美國魯賓博物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