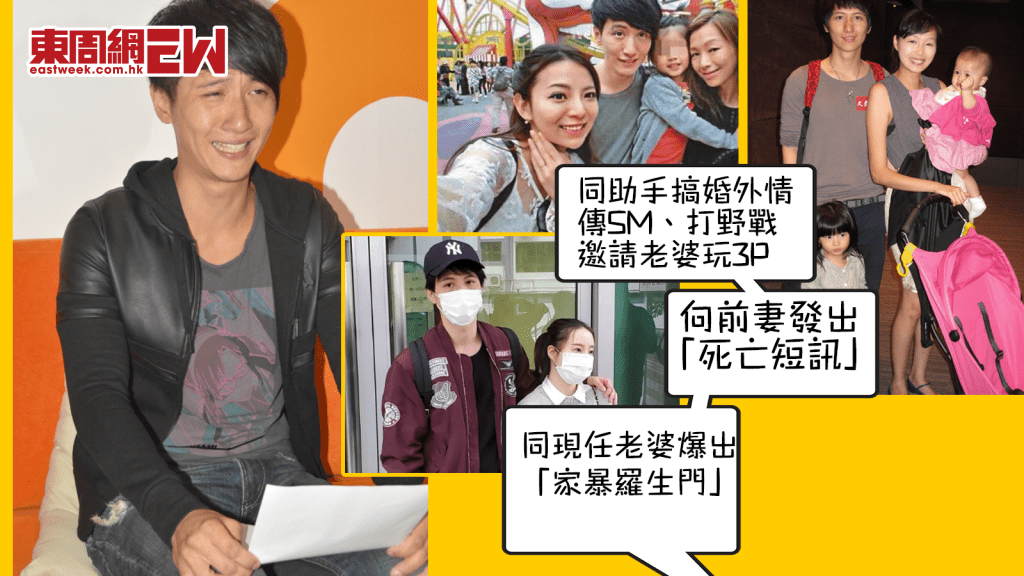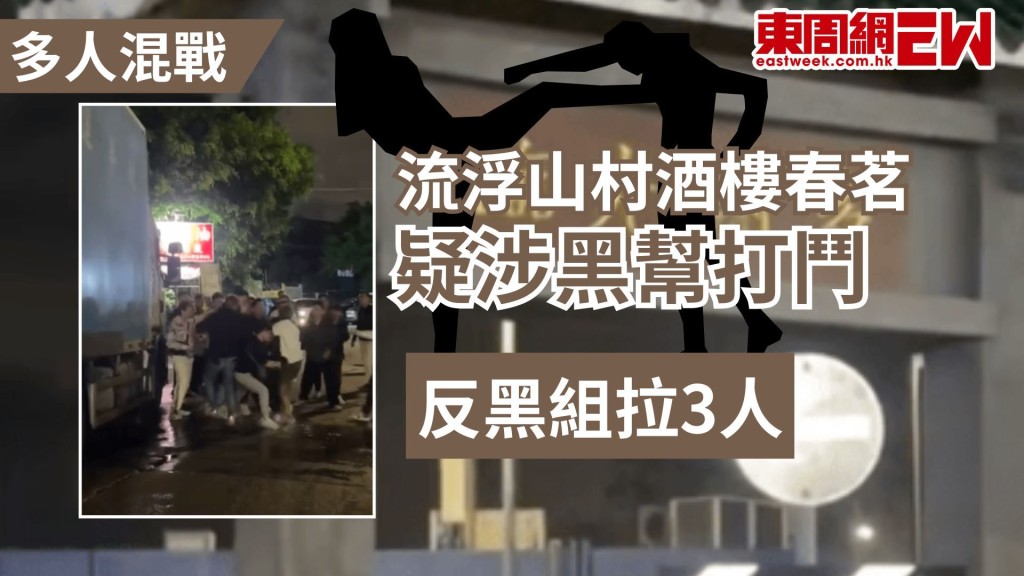二零零三年的愚人節,哥哥—張國榮選擇了在最高的地方,放下最低落的心情,結束四十三年傳奇人生。二十六年的歌影視生涯,留下經典無數。其中在一九九三上映的電影《霸王別姬》,更讓程蝶衣一角在翌年的日本電影影評人大獎中,榮獲最佳外語片男主角。二十二年過去,哥哥的絕代芳顏縱不復見,但文華東方酒店外,「哥迷」依舊赴約,到場獻花憑弔。
現實生活中,像程蝶衣一樣「不風靡不成活」的藝術家,也絕非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。日本當代藝術家草間彌生,曾於一九七三年回國後,到一所精神病院自行登記入住,至今仍一直於院中生活、創作。
自小飽受幻覺困擾的草間老師,在其自傳中憶述兒時初嚐「自我」被幻覺所淹沒之經歷:「某天,看見紅花花紋的桌布後,我把目光轉向天花板時,赫然發現整片玻璃窗和柱子都貼滿了紅花的形狀。無論房間或是身體內,似乎全宇宙都被花給填滿。於是我消融了自我。」幻覺的枷鎖除令她極為驚恐,試圖掙扎逃脫,也讓她切身處地地體會到自我的虛無和無限空間的存在,並啟發了草間彌生式的「自我消融」(self-obliteration)藝術創作歷程。
大概芸芸眾生皆是草間老師口中的「執念藝術家」,從出生到往生,也逃不過「觸、受、愛、取」,以致煩惱覆心。草間認為人類因自身慾望而產生各樣紛爭與戰亂,因此需要忘卻自我和自身形態,與大自然以及外境合而為一,方能進入宇宙的「無限」空間—草間招牌式的「無限的網」。
《華嚴經》云:「一即一切,一切即一。」佛教認為世間萬法都是依因緣而生滅,一切講求眾緣和合。而「自我消融」並非勸人消滅自性,而是鼓勵人們反觀自性,透過浩瀚的自然,以智慧觀照萬物和自身的渺小,以及同一與相互連結之關係,進而在慈悲與平等中重生,這些悉是草間老師從痛苦經歷中歷練出來的感悟,如同諸菩薩皆以救護眾生、與樂拔苦為自身解脫的慈悲法門一樣,無不是從脫去「自我」外衣,去追求「無我」,實踐「大我」。